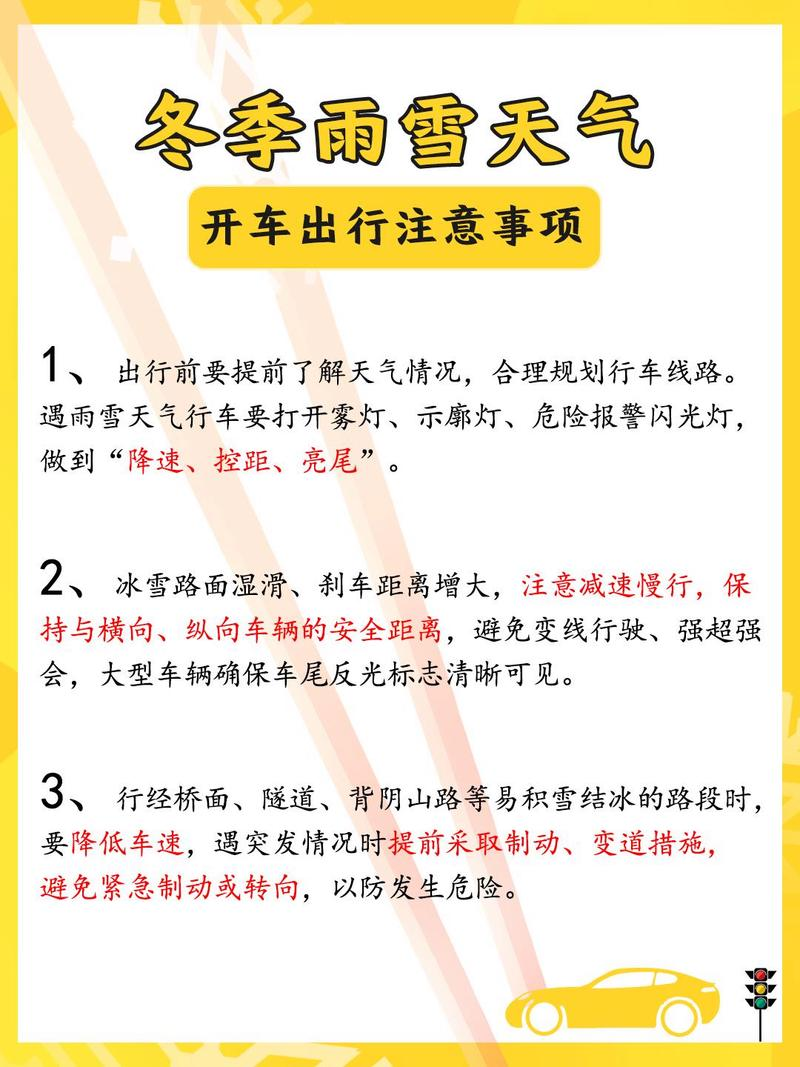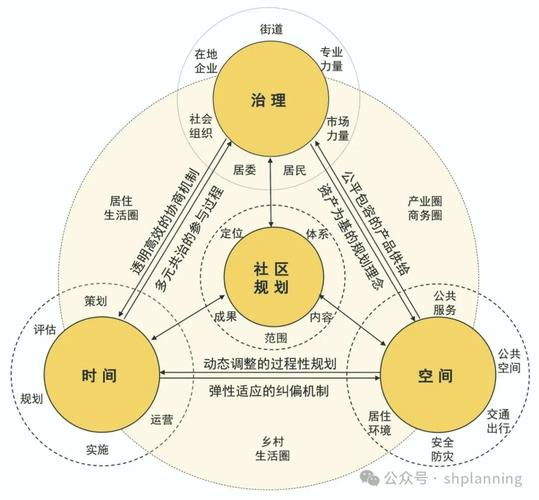版本: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4月
首先得确定知识分子之所指。这个问题,大概从“知识分子”的概念传入中国,便有争议。百年以来,从无休止,不知浪费了多少口水和笔墨。甚至衍生了一些枝蔓,如公共知识分子之争,以及从公共知识分子到“公知”的污名化等。不妨断言,这一切争论,都与知识分子的定性之含混脱不了干系。
拿眼下这场论战来说。针对徐贲所强调的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,张鸣反驳:“什么叫知识分子?如果按照西方流行的定义,有社会担当,有公共责任的人才算,那么,现在中国绝大多数从事知识性工作的人都不是。……如果徐先生的知识分子是指具有自觉具有公共责任的这部分人,当然沉默是不对的。那就意味着你放弃了你承诺的责任,当然,也就不是知识分子了。”
倘若张鸣的质疑成立,那么徐贲对知识分子道德责任的强调,显然失去了批判意义,而变成了一种对身份的确认:知识分子本该具备道德责任,若不具备道德责任,便不是知识分子。争论至此,陷入僵局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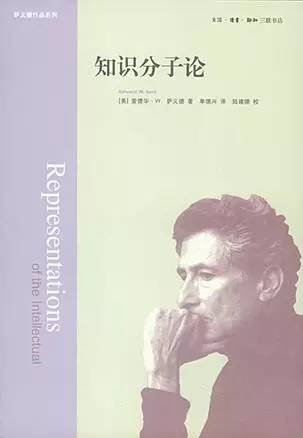
《知识分子论》
版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 2013年4月
所以还得回到定义。萨义德《知识分子论》列举了二十世纪对于知识分子最著名的两种描述,一者来自葛兰西《狱中札记》,一者来自班达《知识分子的背叛》,他采纳了后者的定义:
“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,也不是建立共识者,而是这样的一个人: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,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、现成的陈腔滥调,或迎合讨好、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者传统的说法或作法。”
照此定义,符合标准的中国知识分子简直屈指可数,徐贲与张鸣的争论近乎无的放矢。鉴于此,我更愿意接受葛兰西的定义:
“知识分子指与知识生产或分配相关的任何领域工作的每个人。”
这样的知识分子,是否必须承担道德责任呢?我则持保留意见。
“知识分子”与鞋匠并无道义之别
按照我们的传统,知识被道德化,知识分子自幼被教导,要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,这使他们背负了重于泰山的道德包袱,甚至构成了他们虚弱的生命所不能承受之重。这一传统,绵延至今,尤其汇合了左拉等所塑造的西方知识分子传统之后,导致国人对知识分子的道德预期愈发高涨。我却以为,知识分子,包括公共知识分子,以制造、传播、出售知识为业,作为一门职业,与木匠、鞋匠、厨师等并无道义之别。他们若愿承担道德责任,抨击不公,声张大义,固然可贵;不愿承担,与木匠、鞋匠、厨师等一道保持沉默,只要不曾作恶,那也无可厚非。

《知识分子与社会》
版本: 中信出版社 2013年8月
我最欣赏的知识分子王小波先生曾说过: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,成为思维的精英,比成为道德的精英更为重要。这么说,不是不讲道德,而是换一个角度,来考量道德。如王小波所云:“认真地思索,真诚地明辨是非”,“不计成败利钝地追求客观真理”,此即知识分子的美德。如果一定要强调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,我更希望把道德标杆定位于此。这种道德,或者称之为本分,每一个知识分子都该具备,不容推卸。
我无意与两位先生争辩,更无意调停他们的纠纷,只是试图指出,这场争论不乏错位之处,正源于他们所使用的概念,或者面目模糊,或者歧义横生,譬如对知识分子的定性,以及知识与道德的关系。这些问题,不仅造成了徐贲与张鸣的撕裂,还指向现实的撕裂。就目前来看,这种种撕裂几乎无可弥补,我们只能一面使用撕裂的概念,一面加剧概念的撕裂,正如一面使用匮乏的话语,一面加剧话语的匮乏。
沉默还是呐喊,是困扰每个公民的难题
那么,请允许我投机取巧一把。我以为,与其强调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,不如强调每一个人的公民责任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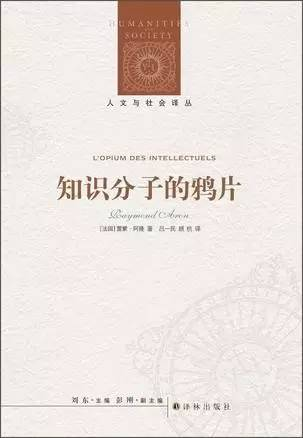
《知识分子的鸦片》
版本: 译林出版社 2012年6月
这不只因为,知识分子的定义暧昧不明,难以达成共识,公民的定义相对明晰,容易凝聚力量;更是因为,徐贲与张鸣所争论的议题,沉默还是呐喊,并非只是困扰知识分子的难题,而是困扰每一位公民的难题。
须知公民的范畴远远大于知识分子的范畴,知识分子背后,还有“沉默的大多数”,农民何尝不该发出自己的声音,工人何尝不该发出自己的声音?社会之进步与发展,人人有责,不能单单依赖知识分子,知识分子更不可以此自命。一旦把目光从知识分子拓展到公民,道德责任等令人纠结的问题,便可不攻自破。
说到公民与公民责任,徐贲和张鸣,非但不是论敌,反而恰成同道。这二人虽在争论知识分子该不该沉默,现实之中,皆以敢言、敢于呐喊著称,不妨说,他们都是公民楷模。这场争论的意义亦在于此,如徐贲所言:“讨论沉默,而不是对沉默保持沉默,这本身就是一种公共意识的觉醒和公民觉悟的进步。”
新京报书评周刊
ibookreview
投稿&合作邮箱:ibookreview@163.com